嘉宾简介
李家洋,植物分子遗传学家,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, 2018未来科学大奖-生命科学奖获奖者。

划重点
1.育种家最大的贡献就是用最少的资源投入创造出最高产、最优质的品种,并且能够适应环境变化。
2.未来育种五代技术是智能智造技术,能够主动响应环境。
3.我希望未来可以创造出大家所需要的新产品,吃着好吃,吃着健康,价格也合理。
出品 |搜狐科技
作者 |周锦童
编辑 |杨锦
“我希望未来可以创造出大家所需要的新产品,吃着好吃,吃着健康,价格也合理。”这是植物分子遗传学家李家洋朴素的愿望。
然而,想要实现这个愿望,却没有那么简单……
一碗香喷喷的米饭的背后可能蕴藏着成千上万个基因的“协同作战”,凝结着李家洋和团队对光照、温度的精准调控。从实验室进行基因测序,再到田间地头进行试验,李家洋正一步步揭开植物性状背后的遗传奥秘,勾画着未来智能育种的新图景。
在未来科学大奖十周年的庆典期间,搜狐科技对话了李家洋教授,听他深入探讨了植物分子遗传学的新进展、基因编辑如何让“设计作物”走向现实以及如何从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到满足个性化需求的。
李家洋表示,植物的性状从来不是单个基因决定的,一棵水稻的高矮、穗粒大小,可能由数十个基因共同控制,所以他们要找出控制关键性状“主效基因”,也要摸清那些“辅助基因”,更要破解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络。
他以粮食作物水稻和模式植物拟南芥为材料,研究植物激素的合成途径与作用机理,解释这些植物株型形成的分子机理。他还致力于水稻分子品种的设计,培育高产、优质、高抗、高效的新品种,像“中科发5号”“中科发早粳1号”和“中科发早粳23”都是出自他的手笔。
在李家洋看来,育种家最大的贡献就是用最少的资源创造出最高产最优质的品种,并且能够适应环境变化,未来还要适应不同的人群。现在他们已经有针对糖尿病人士设计出的低GI(升糖指数)的品种了。
谈及未来的目标时,他表示:“未来育种是自动化、机械化、信息化和专业化加在一起的,我们实验室在未来5-10年内最重要的目标和使命,就是建立智能智造体系,培育智能品种。”
以下为对话实录(经整理编辑)
媒体:您可否科普一下,植物分子遗传学这个学科在研究什么?
李家洋:我们常说的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,“像”,说明是遗传的,“不像”,就是变异。植物遗传学研究的就是从上代到下代的遗传的规律是什么?物质基础是什么?有什么机理?不同的地方是什么?为什么有变化?
比如:有的玉米棒很大,有的特别小,可以炒菜用;西红柿有大的,也有小的,它虽然小但它还是西红柿,这就是遗传“像”的一部分,“不像”的是从大果子变成了小果子。我们的研究探讨是怎么发生变化的,如何让产量更高、品质更好,营养价值更高。
媒体:可以举例讲讲您的研究技术或者方法吗?
李家洋: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不论是植物、微生物,还是人类,最核心的、可以看到的东西用一个词来讲是“表现型”,这是由基因决定的。基因决定所有的性状,比如植物的高矮、分支的多少、大小、根系深浅等。
像水稻、玉米、大豆,或小麦,每一个物种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基因,每一个基因控制什么性状我们都想要搞清楚,有时是很多基因控制一个性状,一个基因也能影响很多性状。
比如我们想让玉米的穗更大一点、结的多一点,那我们就要找出哪些是控制穗子大小的主效基因,哪些是次要基因。有时候一个基因不只影响穗子的大小,可能还会影响植株的高矮、病虫、干旱的响应等,我们要弄清楚其中的相互关系,这也是植物学家、植物理论学家要解决的所有问题。
媒体:有些植物周期很长,那要怎么研究其中的关系呢?
李家洋:有各种各样的方法。因为不同的物种都有相似性,我们可以找一个生长周期短的,大致性状都包括了的“模式材料”,比如拟南芥,生长周期6周比较短,如果把光、温、营养再调整一下,可能三个星期就可以了。
像水稻一般来说要种100多天,(生长周期)是120天到150天,但在特别好的光温水热条件下,60天就能收获,这样一年就可以收割5至6次。
媒体:我们改变种子的时候,改变的是什么?
李家洋:实际上是要改变基因本身的结构,就是基因编码。所有的物种都有基因组,脱氧核糖核酸,也就是DNA是构成基因组的基本单位,碱基对是形成 DNA 、RNA单体以及编码遗传信息的化学结构。
我们要搞清楚那一段DNA它到底起什么作用,是确定蛋白质,还是决定其他辅助基因,这里就涉及到基因的表达调控,形成一个复杂且精准的生命调控系统,要研究从种子萌芽开始到生长、开花、结果整个周期,每一段DNA起到怎样的作用,怎么被表达出来,从而展示它的意义。
媒体:我们如果想在一个环节“做手脚”,该怎么操作?
李家洋:在DNA这部分进行基因编辑,像转基因也都是在这个环节做的,它是根本。就像文章一样,改变了里面的字,表达的意义就会不一样。当然也可以在其他环节去改变,比如把影响基因表达的物质放进去,可能不一定会遗传下去,但可以改变当代基因组里基因表达的顺序和强度,现在在人类的基因治疗上已经做到这一点了。
媒体:改变植物、动物或者人的遗传基因的方法技术有什么不同?
李家洋:人和动物、植物,其实站在规律这个角度来说是一样的。但是里面有非常大的不一样。比如从结构上来说,人的细胞是动物细胞,动物细胞没有细胞壁,但植物细胞有“钢筋混凝土”做的细胞壁,像坚硬的外壳,很难改变形式,如果要进行改变,把外来的基因打进去是很大的困难,DNA的递送系统很困难。
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植物需要光合作用,它有叶绿体,叶绿体有一套色素系统,能够接受光能,但人没有,我们需要食物来获取营养,这是本质上的不同。
媒体:那植物之间的差别会小一些吗?
李家洋:说起来小,其实也很大。比如大豆、向日葵是双子叶植物,而小麦、水稻是单子叶植物。区别就是种子在胚中发育是二片子叶还是一片子叶。从遗传角度来说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就有巨大的不同。比如水稻做根系的遗传转化可以做的很好,小麦就很难,大豆特别难。
媒体:您的研究带来了哪些重要成果?
李家洋:我回国的时候,植物分子遗传学还处在早期的发展阶段,那我就要解决学科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。第一个问题,基因是决定农作物性状的根本,那用什么方法能让大家都找到基因呢?我当时研究的是拟南芥,拟南芥当时在国际上基本成熟,但国内没有,在2000年的时候,国际上完成了拟南芥基因组全序列完全测定并公开发表,这也是第一个经完全测序的开花植物。
但这不是我的目标,我的方向是粮食安全,不过一开始就做水稻难度太大了,根本做不起来。所以我用了几年的时间,在96、97年的时候开始做水稻,建立最有效成熟的水稻基因克隆体系,说白了就是把复杂的农作物基因找到,第一个水稻基因于2003年在自然杂志发表,在国际上影响是非常大的。
第二个,光找到基因不行,还要知道基因是干嘛的,控制哪些性状机理。比如说之前水稻不好吃,什么基因控制的影响了口感是一个复杂的“网”,我们都不知道,所以要把基因找到,我也在开发一些新方法,把高产、优质的品种做出来。这是个例子,那以后玉米,包括蔬菜都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研究。
第三个是我提出了分子设计育种的概念,最后我们用了8-10年的时间,把这个系统做出来了,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新设想,希望未来可以实现智能作物智能培育。
媒体:想达到理想的品种有哪些困难?
李家洋:育种和基础研究不太一样,基础研究是把机制搞清楚可能就会影响很大,甚至获得诺贝尔奖,但育种是做产品,产品是多重因素决定的,要综合性状好,比如光穗大不行,能不能抗旱、抗低温、抗虫,好不好吃,都决定这个品种能不能推广出去,所以要考虑产量、品质再加上环境的影响等等。
媒体:您觉得水稻培养在理想状态下最终会达到怎样的效果?解决多大的问题?
李家洋:这是国家的战略。育种家最大的贡献就是用最少的资源创造出最高产最优质的品种,并且能够适应环境变化。而且未来还要适应不同的人群,比如针对糖尿病人士,我们要推广低GI的品种,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产品了。
媒体:您当时选择研究的方向是非常有预见性的,您怎么回看当时的选择?
李家洋:每一个时代对科学发展都要有一定的预见性、洞察性。我大学开始接触的是树木,后来在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做硕士的时候研究植物分子遗传学,这就上升到DNA水平,那时大家都在梦想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植物的基因控制着什么呢。后来我去美国正好赶上植物分子遗传学大发展的时期,理论上证明了基因可以控制作物性状,但不知道具体是怎样的,大概在90年代初大家突然间发现科学技术可以把基因找到,并跟性状联系起来,大家都很激动。
那我就想如果要解决粮食问题,是不是基因改造主要粮食作物就能实现了,所以我一定要回国。我想拟南芥的基因组测序早晚都会出来,因为那时人类的基因组测序也启动了,虽然也有很好的机会留在美国,但我还是想回到科学院工作。
媒体:您觉得国内育种达到怎样的水平了?
李家洋:育种阶段的分法不一样,大家不是达成共识全部接受,但大致是可以理解的。1.0时代,主要是漫长的人类驯化阶段,2.0是1930年美国杂交玉米成功之后,到我们国内杂交水稻、小麦等技术的发展,杂交育种是主流技术,二代时间很长。现在有三代四代,或者未来有五代技术,但二代技术还是要用,高一代对低一代是兼容的。
三代是转基因分子标记技术,四代是我们提出来的分子设计育种技术,现在国际上已经都认可了,我们也在水稻上也实现了,做出了很多品种,步子相对来说比较快,也比较好。未来五代技术是我曾经提出的智能品种智能智造技术,又叫“双智”。
虽然跟四代关系密切,但很不一样,因为四代以前不是智能的,到五代能够主动响应环境,比如高温来了,能够主动抗高温打开这个基因,但平时这个基因是关闭的。过去高产不能兼容抗病的,高抗病的又不高产,我认为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最大的出路就是基因要有自己的智能开关,需要的时候打开,不需要的时候关闭。
这个是很难的,现在还在探索阶段。我们有一点成果证明这是可以的,我在2018年合作做水稻协同抗病与高产的研究,我们总结这是智能成果的雏形。五代技术的技术手段也是智能的,比如有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生物技术,有监测收集系统,还有就是物种种植时间也会变短。
媒体:您觉得中国的农业科技,可以为世界解决粮食问题贡献哪些“中国方案”?
李家洋:智能育种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方案,种子的科技贡献率一般在40%-60、70%,其他包括机械、水利、化肥、农药也都有贡献,我们至少要在种子方面在国际科学技术上起到引领和引导的作用,在应对高低温、病虫害方面提供一个基本的、朴实的方案。
媒体:作为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,您对实验室未来的发展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期望?
李家洋:做到“双智”是我们实验室在未来5-10年内最重要的目标和使命,建立智能智造体系,培育智能品种。
媒体:您觉得实现后,老百姓的感受会是怎样的?多久能实现?
李家洋:水稻的个性化品种会短时间内提供给消费者,这个技术5年基本框架是没问题的,我觉得大概10年就会有先导性的品种出来,我在2000年左右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,可能觉得有点“天方夜谭”,但实际上我们第一个设计的育种品种出来就是在2017年,现在做的还会更快一点。因为现在的技术手段更高。
媒体:您觉得农业科学有前途吗?
李家洋:农业的发展是无上限的。未来对农业工人的要求也不一样,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,是农业工人,有产业的分工。比如我十年前到以色列农场去,不到100平米的农场里98%都是大学毕业生,会跟我谈抗病调控、营养品质,他们做出来的产品附加值很高,像圣诞节前后还会出口欧洲这些“高大上”的农产品。
我想未来肯定是这样的,是自动化、机械化、信息化和专业化加在一起的,比如会设计程序自动监测,看什么时间需要打药、施肥等等。
媒体:所以未来学农的,以后可能要跟学人工智能的一样了?
李家洋:肯定要懂人工智能,不懂人工智能怎么行?到未来就不只是现在的这种关注植物的生长、开花这种简单的技术了,未来你一定要紧跟科学技术发展。
媒体:您接下来的小目标是什么?
李家洋:希望未来可以创造出大家所需要的新产品,让大家吃着好吃,吃着健康,价格也合理。比如,我们选育成功了双季早粳稻,平均亩产在500公斤以上,具有抗逆性强、株型优、米质优、食味佳等优点,我们希望在未来5年内,让更多的人可以早点吃上优质大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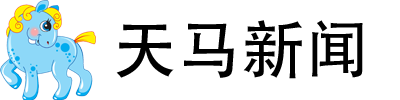
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




